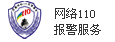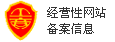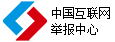我的家鄉離有名的貴州省從江縣“侗族大歌之鄉”小黃不遠,只有30多里地。
小的時候就聽說小黃這么一個地方,聽大人們說話的語意,在我的印象中那里是人間的天堂。到我讀中學的時候,記得有一年暑假,村里來了一群幫少勞力的人家收割稻谷的小黃人,那幾天晚上村子里很熱鬧,寂寞了多年的鼓樓歌聲悠揚,優美動聽的侗族大歌在寂靜的山村的夜晚聽起來別有一番韻味,仿佛那是來自天庭的仙樂。
每當晚飯過后,鼓樓里聽歌的人總是把唱歌的人圍得里三層外三層。還很炎熱的初秋的夜晚,小黃那幾個人帶給村民們許多快樂。那時候我就想,小黃的人都這樣天生一副好歌喉嗎?那里真的如大人們所說的象天堂一樣?
參加工作后,因為工作關系,我便有幸多次到過小黃。隨著到過次數的增多,每次的感受都不一樣,每次對小黃都有一種難以別離的感情。或許是太想用心去貼近小黃的緣故,才一次又一次發現小黃居然有許多讓我對人生還沒有感悟的東西,自己原以為清晰的印象在一次次偶然的發現和啟迪中又變得有些模糊起來——生活中的許多東西總是讓我一時難以悟透,卻覺得又如此的美好和微妙。
我第一次到小黃是在從江縣舉辦第一屆侗族大歌節那年的晚秋,聽說有記者來拍電視,村里十分熱情。村委的負責人把我們安頓在一戶條件較好些的人家,說晚上才能拍到我們要拍的鏡頭。
趁著太陽還沒落山的空閑,我便和同行的搭檔一邊扛著攝像機在小黃四處轉悠拍些外景,一邊留心觀察這個心儀已久的侗家山寨。
小黃是從江縣高增鄉的一個行政村,距離縣城30多公里;全村700多戶3000多人口,全部是侗族。一條清水潺潺的小河穿寨而過,花橋木樓倒映水中,村子四周青山環抱;斜陽下的小黃人家炊煙裊裊,好似一幅美麗的田園景畫。由于這里鄉土風情濃郁,有名聲遠播的侗族大歌,先后被國家文化部和貴州省文化廳命名為“民間文化藝術之鄉”、“侗族大歌之鄉”,是從江縣重點開發的一個原生民族生態文化旅游景點。
這個季節已是農閑,村里到處見到一群群嬉戲的孩子和聚在一起閑聊的大人。這里的人十分和善,見到我們這些陌生人,都十分友好地打著招呼,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親切的笑容,讓人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故友重逢賓至如歸的溫馨感覺。
這個季節也是小黃婦女最忙碌的季節,走在村里的每個巷道,屋檐下、坪子邊不時有三三兩兩的婦女在染布或捶布,見到我們便停下手中的活路玩笑幾句。
讓人醒目的是那些晾掛在木樓下的黑得發亮的一條條侗布——這是小黃一道美麗的風景。這時候行走在木樓晾曬下來的長長的侗布下,聽那一陣陣有節奏的或近或遠的捶布聲,我仿佛在古老的文化藝術殿堂里穿行,感受著小黃濃厚的鄉土氣息,使我不由感嘆小黃侗寨歷史時空的深隧。
到小黃次數多了,也便和這里的人熟識起來,有了許多要好的朋友。如果不和小黃人深交,很難洞察到他們生活中歷經過的滄桑,會使人誤以為人世的風風雨雨悲哀苦痛總是和他們擦肩而過。我發現,對待生活,小黃人似乎比別人要坦然得多,一生中的得失他們很善于平淡面對——他們總是那樣寵辱不驚。后來我才發覺,原來小黃人是那樣的熱愛生活,他們以一種特有的坦然和開朗的性格善待自己的一生。難怪有學者說小黃人豁達。
在小黃人的面前,不管是學識淵博的學者還是目不識丁的百姓,不管是享有厚祿的高官還是一無所有的布衣,即便是短暫的相處,總是會讓人不由自主地忘卻此時的自己,人生所有的煩惱和雜念,在這樣的環境中煙消云散,步入一種輕松快樂自由的人生境界。小黃人的處世哲理是那樣的深刻和公平,高低貴賤之分在他們面前常常顯得如此無地自容。
其實小黃人的開朗僅僅是熱愛生活的一方面的表現,生活中的苦難他們一般都不會在別人面前——尤其是公共場合顯露出來。小黃人的的情感世界十分豐富,世襲的民族地域文化和傳統的鄉俗思想觀念,鑄造了小黃人樂觀、堅強的性格。
在一次歌會上,我見到了一位剛剛失去親人的小黃的吳姓老人,我和他十分熟識。這次他沒有走進歌堂,只是倚在鼓樓外面的一根偏柱上靜靜地看著同伴放聲歌唱,那神情仿佛是依托這樣的氣氛,在深深思念著另一個世界里的親人。他的臉上的表情看不出任何的快樂和悲傷,此時此刻我真的難以猜測他是怎樣的心情。他是以這樣的一種方式吊祭已故的親人?還是用這樣的氛圍撫慰心中的悲痛?
我沒有過去和他攀談,此時我能對他說些什么呢?過一會兒,我再留意他倚的那根柱子時,才發現他已經走了,另外一位老人又倚到了那根柱子上。在此后不久的幾次歌會,我在歌堂上又見到了他,這時他已經和同伴們一起坐在鼓樓里同聲放歌。
我有時常常被工作或生活上的一些瑣事攪擾得煩惱不已,每當這時候便回想起在小黃的情景,煩燥的心緒就讓小黃人坦然處世的心態平靜下來。在世事難料的現實生活中找到真正的自己,用平淡和愛心去對待迎面而來的每個日子,才是最好的善待自己人生的尋找幸福方式。
小黃人很聰慧,也很爭氣。一次和小黃一位要好的朋友交談時他告訴我,家里以前很窮,他小學沒畢業就輟學務農了,為的是分擔父母的農活好讓在縣里讀中學的哥哥安心讀書。哥哥也果然不負家里的期望,考上了大學,畢業后先是在深圳一家外企當英語翻譯,后來自己又開了一家小公司,生意還挺不錯。在小黃我還認識了一位朋友,她初中畢業后由于家里經濟條件沒機會讀高中,在外打工的幾年時間通過自學考上了省外的一所大學。我問她畢業后想找什么樣的工作?她說這些都無所謂,其實當時讀書只是想證明自己的能力。她告訴我,今后如果經濟條件允許,還想考研。
與他們交談,我為自己曾因挫折而煩惱的往事感到慚愧,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一種自強不息奮發向上的可貴精神,這種精神一直在激勵著我奮進。和他們相比,我認識的大多數人的條件比他們好得多,但缺乏這種精神的的確實在不少。
說起小黃不能不說這里的歌。許多人都知道,小黃是出了名的“侗歌窩”,早從50年代開始,小黃人就把侗族大歌先后唱到了北京唱到了海外,傾倒了無數的國內外觀眾。這里的侗族大歌被音樂界權威人士喻為“清泉閃光之音樂”。這個榮譽是受之無愧的。多聲部無伴奏的侗族大歌,其優美的旋律以及巧妙的模仿大自然聲音的演唱技巧,世界上能像侗族這樣創造出來的這天籟般的原生態音樂的民族恐怕為數不多。侗族大歌在貴州、廣西、湖南等省(區)的侗族地區廣泛傳唱,而小黃人演唱的侗族大歌又別有一番韻味。在多次舉辦的“多彩貴州”歌唱大賽上,民族原生態唱法中小黃侗族大歌隊每每摘冠;小黃侗族大歌獨特的藝術魅力,使許多專家學者為之驚嘆并認同了這個觀點。
很難想象,在一個擁有數千人的侗寨,從會開始說話的孩童到老態龍鐘的白翁,人人都會唱歌,人人都愛唱歌。在小黃的現實社會生活中,侗族大歌無處不在。歌也是他們創造美好生活的良方,那里真的像天堂。
我多次看到小黃舉辦的不同規模的侗歌演唱活動,那場合那氣勢令人震撼,當宛如天籟之音的侗族大歌響起,人仿佛置身于音樂的海洋,那旋律那節奏讓人激情澎湃,在那樣的場合每個人都像是一個跳動的音符。
小黃每年都舉辦不同規模的侗歌演唱活動,近幾年來在當地政府的引導下又在每年的11月28日舉辦了侗族大歌節,還把侗族大歌引進了當地學校的課堂。在小黃共有不同年齡段的歌隊50多個,男女歌師100多人,而且每個歌師都有自己的歌堂和學生。剛開始學語的孩童首先學的就是侗歌,在那樣的環境中,小黃人就是這樣伴著歌聲一天天地成長。小黃是“侗族大歌之鄉”,名副其實。
前些天有小黃人來告訴我,今年農歷的八月十五他們又將如期舉辦一年一度的侗歌大賽,還邀請了鄰寨的歌隊一起來參加,希望我到時也去。這時我突然覺得,該為小黃寫點東西了,以前雖然拍過一些關于小黃的電視專題片和新聞,但是畢竟離當地政府授予我這個“榮譽公民”的期望和要求還很遠。寫些什么呢?這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對小黃還有那么多想不透看不清的東西。或許如小時侯聽大人說的那樣,小黃是“天堂”;對于這個“天堂”,直到現在我仍然還只是個印象而已。


 新聞熱線:0855-8222000
新聞熱線:0855-8222000